- 徐有富:论引文与引文注释
- 时间 : 2018-11-13 21:27 来源 : 南雍论学 作者 : 徐有富 点击 :
-
【本文原载《古典文献研究》,2004年第1期。文中部分内容可参见徐有富著《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283-287页。“南雍论学”微信版进行部分删节,引用请据原文。】
引文与引文注释是学术论著的重要内容,一些学术论著尚不够重视,某些引文与引文注释也不够规范,今略加探讨,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引文与引文注释的意义
学术论著与文献整理成果往往需要引用已有文献资料,并详细而准确地注明出处。这样做是为了提供文献依据;反映研究工作的起点,占有资料的多寡、深浅与新鲜程度;同时也为读者继续研究相关课题提供资料线索;还能表明已有科研成果的归属,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到,有关本课题,前人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作者新的贡献在何处,同时也简化了论证的过程。这样做也有利于对作者及其论著,以及出版与发表该论著的出版社或期刊的学术水平进行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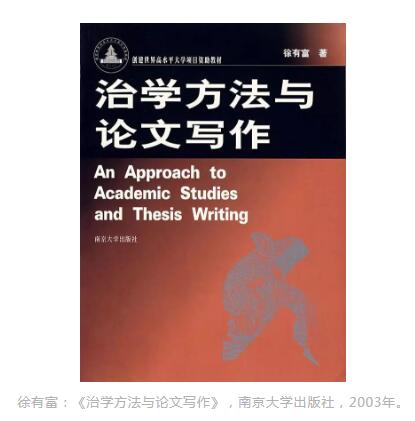
总的来说,引文注释是衡量论文作者的学术态度、学术水平、资料占有情况等的客观标志,有利于读者复核原文,判断资料的真伪、可靠程度与价值;还能使论著建立在可靠资料的基础上,有利于培养作者严谨踏实的学风。现择要述之如下:
1.提供论据
唐人刘知几《史通·杂说下》指出:“向、雄以后,颇引书以助文。”其实在两汉以前,人们写文章,为了增强说服力就已经注意引经据典,所以我们在读先秦典籍时,经常会遇到“子曰”、“《诗》云”之类的话。引文主要作用就是为自己的论点提供论据。
比如现代著名唐史研究专家岑仲勉在《中外史地考证·前言》中说:“汉唐在玉门关西未见驿传之记载。”严耕望不同意这种观点,指出:“岑先生意谓玉门关以西到了元代才开始置驿传。其实唐代玉门以西早已置驿,而且史料极多。”接着他举了五个例子。其第二个例子为岑参《送刘单赴安西便呈高开府》诗:“曾至交河城,风土断人肠。塞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县之西北,当然在玉门关以西了。
再如,胡应麟称王维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为“五言绝句之入禅者”,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引用禅宗创始人慧能禅师在临死时说的一段话:“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静寂,即是大道。”两者所描写的静寂境界何其相似。有了确凿可靠的相关引文,你的论点也就有了说服力。
2.肯定前人的研究成果
科学研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迈进的,引用前人的科研成果,并详细注明出处,就能对前人的科研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明方以智《通雅》卷首《凡例》云:“此书必注引出何书,旧何训,何人辨之,今辨其所辨,或折衷谁是,或存疑俟考,便后者之因此加详也。士生古人之后,贵集众长,必载前人之名,不敢埋没。”
显然这样做还涉及到学术道德问题,因为引用别人的科研成果而不注明出处,难免有掠美之嫌,也就是不道德的行为。而要求引文详细注明出处则有利于培养诚实、严谨的学风,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抄袭行为的产生。例如在讨论李陵、苏武五言诗的真伪问题时,人们都喜欢引用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中的一段话:“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还有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四《李陵》中的那段话:“《文选》编李陵、苏武诗,凡七篇,人多疑‘俯观江汉流’之语,以为苏武在长安所作,何为乃及江汉?东坡云:‘皆后人所拟也。’予观李诗云:‘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为可信也。”显然,这样做有利于明确各人在李陵、苏武诗辨伪方面的成就与责任。
引用已有科研成果也能简化论证过程,譬如清人王梦阮和沈瓶庵写过一本《红楼梦索隐》,认为《红楼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董鄂妃即秦淮名妓董小宛。这当然是荒谬的,但是你要反驳它,三言两语还真不容易讲清楚。我们不妨引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董小宛做妃的道理。”这段话很有说服力,就无须我们再费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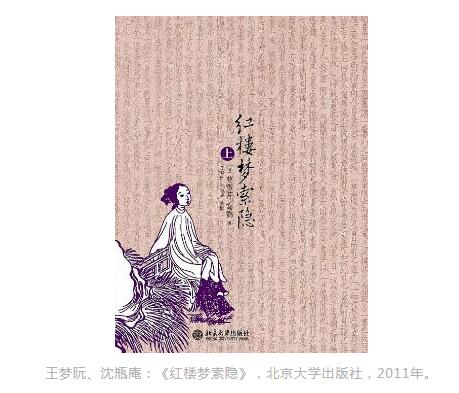
3.为研究相关课题提供文献线索
如果我们研究神话,不妨读一读袁珂所写的《中国古代神话》(中华书局,1960)。该书虽然是用白话文写的,但是作者将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不仅注明了原文,而且还注明了出处,这为我们搜寻与核实原始资料提供了方便。我们在研究某一课题时,从相关学术论著的注释中,能够找到所需要的资料来源,我们当然不会拒绝利用它们。
注释一般都广征博引,特别是一些早期注释,所引资料多已亡佚,则其注释不仅指出了资料线索,而且还提供了珍贵的较为原始的资料。《四库全书总目》于《世说新语》提要称:刘孝标“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清沈家本撰《三国志所引书目》,辑得210家;《世说注所引书目》,辑得414家。
集注(含集解、辑释、会笺等)实际上是注释资料的汇编,如清王琦的《李太白诗集注》、清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清王先谦的《庄子集解》。今人也出版了不少资料丰富的集注本,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该书以明汲古阁刊《唐人八家诗》之《李义山集》(三卷,不分体)为底本,以八种明清印本、抄本为校本,复以唐、宋、元三代六种总集进行校勘。该书之注释笺评,汇集了十一种笺注本的成果,“复旁搜宋以来诗话、笔记、选本、文集中有关评注考证资料,近人及今人研究论著中有关注释、考订方面之资料亦酌加采录。”
有的注本虽无集字,实际上也是集注本,如王仲闻的《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将有关各作品的评论资料,以《参考资料》的名义,附在各作品之后,如《声声慢》(寻寻觅觅)之后共附参考资料28则,在书后《参考资料》部分共附传记34则;诗词评论36则;其他资料10则。当然为人们从事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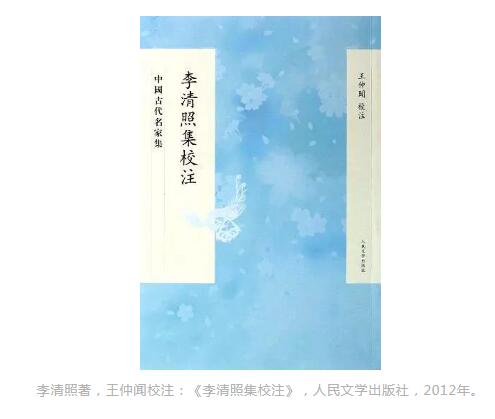
4.有利于判断引文的资料价值
胡适在《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中指出:“辑佚书必须详举出处,使人可以复检原书,不但为校勘文字而已,并且使人从原书的可靠程度上判断所引文字的真伪。清朝官书如《全唐文》与《全唐诗》皆不注出处,故真伪的部分不易辨别。例如同为诏敕,出于《唐大诏令集》的,与出于契嵩改本《六祖坛经》的,其可靠的程度自然绝不相同;若不注明来历,必有人把伪作认为史料。万里先生此书每词注明引用的原书,往往一首词之下注明六、七种来源,有时竟列举十二、三种来源,每书又各注明卷数。这种不避繁细的精神,是最可敬又最有用的。”
为了提高资料的可靠程度与使用价值,近人编纂校辑的书籍,一般都对引文的史料价值进行鉴别,并详细注明引文出处。如隋树森《全元散曲》自序云:
总集中所收的作品如果不注出处,对读者是非常不方便的。《全元散曲》在每首曲子的末尾,不仅注出它最早见于何书,并且把其他选有这首曲子的书名,也不厌其详地一一写出。套数里面的一支或几支曲子,有被《太和正音谱》、《北词广正谱》、《九宫大成》等曲谱征引的,也注在该套的末尾。这对读者至少有这些方便:一、把材料来源向读者作了交代,读者如果觉得有什么问题,可以覆检原书。二、读者看了书名,就很容易知道某一首曲子都有哪些选本选过它,因此也就知道哪些曲子以往比较为人们所喜爱。三、专家们根据所注的书名,可以判断把这首曲子归某一作家,其可信的程度如何。
二、引文与引文注释存在的问题
引文并注明出处的做法起源甚早,如先秦典籍《左传》、《国语》就经常引用《易》、《诗》、《书》中的话。但是引文与引文注释还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现也择要略述如下:
1.删节原文
引书者各取所需,将自己认为不必要的词句删去,应当说是正常现象。但是古代著书撰文,通常不用标点符号,因此被删去的部分,作者难以表明,读者也难以发现。直到普遍使用标点符号以后,有的学者仍然主张不用省略号,如陈垣先生。
他的学生说:“援庵师甚不赞成引用史料以‘……’符号,表示删省。曾说:‘史学家竟不敢删省前人之文,如何能自成一家之言!’所以陈先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有省略而无改动。因为援庵先生认为他是在写历史,只要注明根据何在,就尽到史家的责任,删掉不必要的字句,是史家应作的事。”
因此,如以为引文同原书一模一样那就错了,如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卢文弨绍弓》引钱大昕《群书拾补序》云:
抱经先生精研经训,(博极群书,)自通籍以到归田,铅椠未尝一日去手。奉廪修脯之余,悉以购书。遇有秘钞精校之本,辄宛转借录。家藏图书数万卷,(皆)手自校勘,精审无误。(凡所校定,必参稽善本,证以他书,即友朋后进之片言,亦择善而从之,洵有合于颜黄门所称者。)自宋次道、刘原父、(贡父、楼大防)诸公,皆莫能及也。
括号内是被省略的部分,如果从校勘学的角度看,被省略的部分,恰恰是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我们按照《藏书纪事诗》转引这段材料,那就贻误读者了。
2.隐括原文
古人引文有隐括原文之例,如陈澧《东塾未刊遗文·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云:“所引之书,其说甚长者,当择其要语,或不必直录其文而单浑括其意,如孔《疏》引郑《注》有云‘郑以为者’,此亦引书之一法。”
桂馥云:“古人引经,略举大义,多非原文。如《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引《诗》‘兄弟虽阋,不废亲也。’引《书》‘九族即睦,可以亲百姓。’《说文》引《书》‘洪水浩浩。’此岂《诗》、《书》之本文哉。今人多据《书》、《传》所引以增改经文,虽曰治经,实乱经也,可不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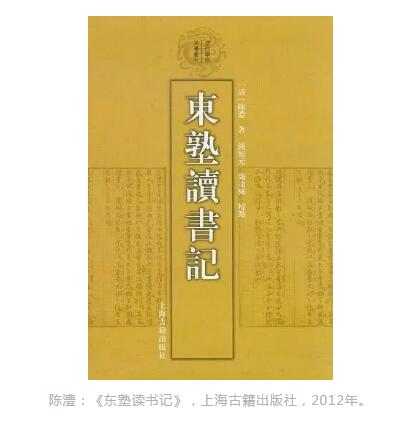
下面我们就再举一个隐括原文的例子。《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引《唐书》曰:“开元十九年命有司写《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以赐金城公主,从其请也。”《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列传》原文却作: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弃隶缩赞联姻,开元十九年(731),“吐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应当说《太平御览》对原文的概括很简洁,但是《旧唐书》的原文说了求书、写书、颁书的具体过程,史料价值更高一些。
3.引文有误
由于粗心大意,引文与引文注释中往往会出现许多文字错误。这种现象在古书中是非常普遍的。如钱大昕批评道:“朱国祯《涌幢小品》三十二卷,好谈掌故,品题人物,不为刻深之论,盖明季说部之佳者。至于援引古书,多有差误。如张彪称其妻为‘乡里’,见《南史》,而误以为杨彪。王文公父名益,而误以为盖。‘止谤莫如自修’,魏司空王昶语,见《三国志》,而误以为《文中子》。”
再如张舜徽《广校雠略》卷四《搜辑佚书论五篇·古人援引旧文不可尽据》举例云:“‘致远恐泥’,子夏之言也,班固以为出孔子。‘其进锐者其退速’,孟子之言也,李固以为出《老子》。孟子以孔子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曾子。”
今人游国恩等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说:“王粲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品》称他为‘七子之冠冕’。”其实这句话不出《诗品》,而出自《文心雕龙·才略篇》。
4.引文注释不规范
引文注释不规范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有一本《常用文言实词讲解》(颜亨福编,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作者在《前言》中说:“为了给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提供参考材料,同时也为帮助语文爱好者和中学生学习古典文学,我们编写了这本讲解文言实词的工具书。”但是这本书无页不错,在引文方面的明显错误就有200多处,与引文注释有关的约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引文出处有误。如55页“小人有母……”的出处不是《战国策》,应是《左传·隐公元年》。60页“折戟沉沙……”的出处不是“杜甫《赤壁怀古》”,应是杜牧《赤壁》。
二是引文作者有误。如《盐铁论》的作者是桓宽,但是书中一会儿是桑弘羊写的,一会儿又成了晁错的作品。
三是所注引文出处过于笼统。如一些引文所注的出处是《尚书》、《三国志》、《齐民要术》、《红楼梦》等,叫人如何查对。
四是相同的出处却注上不同的题名,如同一本书的出处分别注《尚书》和《书经》,同一篇文章的出处,分别注《孙膑》、《孙膑吴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
五是注释格式不统一。如《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竟有七种不同的注释格式。
更为严重的是引用别人的资料而不注明出处,这实际上是抄袭。清人陈澧指出:“前人之文当明引不当暗袭。《曲礼》所谓‘必则古昔’,又所谓‘毋剿说’也。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徵其见闻之渊博。若暗袭为己有,则不足见其渊博,且有伤于笃实之道。明引则有两善,暗袭则两善皆失之也。"(《东塾未刊遗文·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近年学术论著中的抄袭现象十分严重,已为大家所熟悉,我们就不再举例了。
三、怎样引文与注明引文出处
1.尽可能直接引用原文
正因为引文中普遍存在着上述问题,为了保证引文无误,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引用原文,而不要从其他人的论著中转引。顾炎武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
近人唐圭璋也说:“明清人引宋人轶事往往有误,盖因明清人自由剪裁宋人载记,字句俱不符原文,故引用宋人说词之语必须用宋人第一手资料。明人误引宋人书,清人又误引明人书,展转沿讹,贻害不浅。”但是,我们有些人或者学风不够严谨,或者为了节省时间,或者受到条件的限制,找不到原文,人们常会转引别人的资料,即使一些名家也在所难免。下面我们就举一个学术名家由于转引人家的材料而一误再误的例子: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引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都是从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转引的。《史记志疑》中有一段话说:“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钱穆不知道王世贞书名是《读书后》,又没有经过查阅,在《系年》中引用这段话时,加上“说”字,成了“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郭沫若《十批判书》引用这段话时,也不知道王世贞的书名,因而把《读书后》改为《读书后记》。余英时也不知道王世贞的书名《读书后》,他一方面跟着郭沫若将书名改为《读书后记》,一方面又说《十批判书》抄袭《先秦诸子系年》。
陈垣以学风严谨著称,而且专门教过史源学,对于使用原始材料非常重视,而一旦转引别人的材料,也会出错。他的学生刘乃和谈到他“写《史讳举例》时,因是为钱大昕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而作,仓促成书,有些材料就是转引于钱氏,未及细检原书,不免有些错处。该书木刻雕版时,虽有所发现,但已不及改刻,因此一九五八年科学出版社重印时,他让我将全书引文一一检对,他说:‘以钱氏之精,尚且错简、脱落、谬误甚多,用其他人的引文,就更应亲自动手,勤查勤找了,这是省事不得的。’”
2.详细而准确地注明引文出处
我国素有引书注明出处的传统。余嘉锡指出:
引书必著卷数者,为其便于检查,且示有征也。自以帛写书而后有卷数,若用简册之时则但有篇章耳。书之篇第往往移易,故同一书而次序不同;若但引其篇第,无以知其为某篇也。举其篇名,则便于检查矣。故引篇名,犹之引卷数也。《左传》、《国语》引《书》《盘庚》、《泰誓》之类,往往举其篇名,至引《易》而举某卦之某爻,引《诗》而举某诗之几章,则更细类。此自相传之古法,不始于六朝唐人也。
学术著作理应对每条引文都注明出处,有些学术著作只笼统地列了一个参考文献目录,也是不够诚实、不够科学的。裘锡圭在一篇书评中批评道:
作者在前言中说:“在撰写过程中还参考了前人及时贤的不少论著,因体例及篇幅的限制,未能逐条说明……。”我们觉得对这样一部专著来说,不逐条说明所参考的论著,恐怕不是妥当的办法。这使读者失去了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的线索, 并且使他们弄不清究竟哪些意见是作者自己的创见。
学术著作还应当强调注明引文的原始出处,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云:“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譬如马、班并有,用马而不用班。)最初之书既亡,则必标所引者。(譬如刘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见于《汉书·艺文志》。阮孝绪《七录》既亡,而阙目见于《隋书·经籍志》注。则引《七略》、《七录》之文,必云《汉志》、《隋志》。)乃是慎言其余之定法也。书有并见,而不数其初,陋矣。引用逸书而不标所出,(使人观其所引,一似逸书犹存。)罔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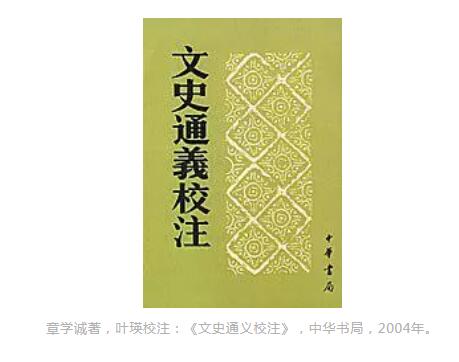
3.不要断章取义
古人引文有断章取义现象,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甚至不惜曲解原文。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就以《左传·襄公十五年》的一段话为例,看作者是怎样断章取义的:“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磋我怀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
被引用的《卷耳》中的这两句诗,显然是指那位女子所怀念的人,正在路上奔波,与能官人实在没有什么联系。但是由于《左传》断章取义地引用了这两句诗,给后人理解这两句诗造成了混乱。
今人引文断章取义的现象也不乏其例,如有篇题为《宋诗怎样一反唐人规律》的文章说:“唐人重抒情,宋人主议论。”为了证明这一点,作者引用了邵雍的一段话来证明宋人是反对用诗歌抒情的:“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但是这段话引得不完整。邵雍完整的意思是:“近代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而这段话恰好说明不少宋人同唐人一样,也是非常喜欢运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感情的。可见断章取义,曲解原文的含义,也就不能做到真实可靠。
4.不要误会原文,妄加引用
我们还要仔细体会原文的含义,不要误会原文而加以引用。如严耕望谈到他“看到一位研究唐宋史的日本名家,引用李白《系寻阳上崔相涣》诗‘邯郸四十万,一日陷长平’,作为唐代邯郸县人口殷盛的证据;不知此句是用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秦大胜坑赵四十二万的典故。”
其实中国学者也有误会原文而用作证据的现象,如谢文利《诗歌美学》第6页第6段有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古存’(韩愈),‘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这字里行间,蕴蓄着对诗仙、诗圣和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何等强烈的赞誉之情。”刘世南分析道: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韩愈的《调张籍》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作者改为“万古存”,大约是想到文天祥《正气歌》的“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了。著书为文似不宜如此粗浮。(二)李白说的“韩荆州”是韩朝宗,唐玄宗开元年间任荆州大都督长史,《新唐书》卷118本传称其“喜识拔后进”,“当时士咸归之”,谢君竟误认为韩愈。试问李白盛唐人,韩愈中唐人。李白卒于公元762年,后六年(768)韩愈始生,李白怎能写诗(其实那两句是当时游士编的顺口溜)表达自己对韩愈的“强烈的赞誉之情”呢。
仔细体会原文的含义,还表现在标点上。对引文标点有误,就说明作者没有正确理解原文。例如,某出版社出版的《菜根谭》中有这几句话:“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屋漏中培来,旋转乾坤的经纶从临深,履薄中操出。”其实,这几句话应该这样标点:“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屋漏中培来;旋转乾坤的经纶,从临深履薄中操出。”胡建逵分析道:
这几句话中的“暗室陋屋”和“临深履薄”两个成对的典故均出自《诗经》。前者语出《诗·大雅·抑》:“相在尔室,尚不愧屋漏”,“屋漏”指古代室内西北角施小帐之处,“不愧屋漏”即喻不在暗中做坏事,起坏念头;“临深履薄”语出《诗·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后因以“临深履薄”喻谨慎戒惧。知此含义,然后以骈偶律其句式,就会将这几句话点断正确。
我们如果发现原文献有错误,在引用时也应当指出,以免以讹传讹。钱锺书《谈艺录》之六十九云:“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诗中之理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是将理藏于形象之中。但是其中的“蜜中花”应当是“花中蜜”,因为花显然有体有痕有相,不符合作者的要求,只有“花中蜜”才是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的。因此我们在引用这段话谈诗的理趣时,应当作必要的说明。
5.引文注释方式
引文注释方式约有四种:一种是文中夹注,这是我国图书传统的注释方式,我们打开一些古书就会发现,正文通常用大字,而注释通常用小字作双行直接附在正文后面。古书难懂,这种方式将正文与注释紧密结合在一起,给读者阅读古籍提供了方便。
现代图书文字多采用横排,于是注释也采用单行,用与正文同号字或小号字,置于圆括号之中,放在引文或其他需要注释的文字之后。其优点是作注便利,正文与注释联系紧密,不易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其缺点是行文累赘,读起来不够流畅。为了避免尾注、脚注过多,一些常见资料或反复出现的资料源可采用文中夹注方式,通俗读物也多采用这种方式。
一种是尾注,即将注释集中置于论文的末尾,这是国外学术论著普遍采用的方式,我国学术论著采用尾注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其优点是保证了行文的简洁流畅,能够集中反映作者的资料占有情况,其缺点是一边看论文,一边翻阅注释有点麻烦,有些粗心的作者容易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即论文中的注释序号与文末的注释不相符合。发表于写给专业人员看的较为严格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多采用这种注释方式。
一种是脚注,即将注释置于引文当页的地脚,用略小于正文的字排版。其优点是保证了行文的简洁流畅,便于读者立即找到引文出处,免除了翻检之劳,也避免了注释序号与注释不相符合的现象。其缺点是不易集中反映作者的资料占有情况,占用版面较多。采用书本式的学术论著多采用这种注释方式。现行学术期刊也多改用这种注释方式。
还有一种是将引文出处融入行文之中不再专门标出,其优点是既避免了学术论文的统一模式,行文又显得较为流畅;其缺点是不易准确细致地注明出处,也不易了解作者占有资料的情况。写给普通读者看的较为通俗的学术论著,多采用这种注释方式。此外容易找到的常见资料也多采用这种方式交代出处,以免引文注释过多的现象。
文章来源:南雍论学 微信公众号,引用请据原文。
